Asia TV 2020-11-15 NewsCenter 851478
冰 凌 短 篇 小 说 :无 花 果
冰 凌





夏了。
门前的无花果,挨着叶茎的枝上,结出卵形的果子,嫩绿嫩绿,一捏,软乎乎的,果尖上开了口,是果⼦熟了。该摘了。
四岁的黑黑,拖着长涎,找妈妈摘果子解馋,可妈妈不见了。
妈妈刚才还在这里,久久地亲着他,还流着泪呢。妈妈到哪里去啦?
黑黑去找爸爸。
爸爸正闷在屋里,一双粗掌抱着脱瓷的茶缸,就着桌上一摊花生米,独自大口大口喝酒,喝得满脸铁青。
黑黑小手抓着桌沿,昂着头问:“爸爸,妈妈呢?”
爸爸瞥了他⼀眼,没有说话。
黑黑呆呆地站着。
爸爸抓起一颗花生米,塞进他的小嘴里,说:“去玩吧。”说完,爸爸抱起茶缸,“咕噜咕噜”连喝⼀气,两眼发出浑光,自言自语:“散了倒好……倒好……天知道……天知道……怎么凑在一起……活受罪……”
黑黑踮起脚尖,又问:“妈妈呢?”
爸爸瞪了他⼀眼,凶狠地说:“走了!”
黑黑眼睛里滚下了泪珠;“我要妈妈!”
爸爸一巴掌抽向他……
夜晚,黑黑睁开红肿的眼睛,仍然不见妈妈。只有爸爸双臂紧紧的抱着他,喷着浓烈的酒气,死睡着。
黑黑想哭,但他看了爸爸一眼,黑黑不敢哭。从他记事起,他从来没有跟妈妈分开过。晚上,妈妈总是搂着他睡觉,但他常常被爸爸妈妈的争吵声惊醒,他恐惧地看看爸爸,又看看妈妈。爸爸披着厚厚的工作袄,狠命地抽烟。而妈妈则搂着他,眼泪一串一串滴下来,滴在他的脸上,滴在他的身上,也滴在他的心上。
妈妈走了。
黑黑纯净的心田,被犁开一道沟痕。
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。
五年了,门前的无花果,已长成树了。树高过墙,干粗如碗,掌状的大叶,层层迭迭,把门前的一大块场地都给荫了。结出的果子,个更大,一咬,肉质更嫩,果味更甜。
这棵无花果,是黑黑生下那年春天,妈妈剪枝栽下的。为的是与黑黑同生共长,做个伴儿,让黑黑从树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跟无花果一样,黑黑也长大了,成了一个九岁的大孩子了。五年,近二千个日夜,在这个闽北林场一隅,他跟爸爸过日子,泡在父爱里长大。只是,在这五年中,他没有再见过妈妈一面。妈妈在哪里?黑黑不知道。他没有去问爸爸,他不敢在爸爸面前再提起妈妈。偶然一次,他听大人谈话,模模糊糊地知道,妈妈好像住在上海,而且有了新家。上海在什么方,他也不知道。一天,他乘放学,老师同学都走尽时,鼓起勇气,赤着脚,用铅笔刀撬开老师办公室的窗户,爬了进去。他站在办公桌上,对着墙壁上的大地图,按着不同的色块,从上到下,一字一字细细地寻找……第二天,他又找,终于在密密麻麻的字海里,找到了上海。他摊开小手掌,把上海跟闽北一连,天呐!还够不着,这要多远啊。
黑黑没有吭声,跑到林场后山的顶峰,爬上一棵大松树,抱着摇摇欲折的枝干,向北边,尽力望去,除了一层层浓淡不等的山,和紧连着的空蒙蒙的天,其他什么也望不⾒。他慢慢下树,一时间仍抱着树身,不愿松开……
这天夜里,黑黑在睡梦里见到了妈妈,就在一步之遥,他摇着胳膊,拼命一挣,嘶声大叫:“妈妈!”叫后惊醒,他使劲揉着惺忪的眼睛,四周望去,没有妈妈,只有爸爸睡在身旁,鼾声如雷。
看不见妈妈,黑黑就想,想得很苦。他想起妈妈很喜欢亲他,弯着脖子,亲得很久,恨不得把他化了,他被亲得直叫唤,这是母爱。但五年过去了,母爱与他无缘了,只有一种对母爱的渴望,日复一日,愈来愈强烈,狠狠地抓着他的心,把他幼嫩的心,抓出一条条血淋淋的痕来。他有父爱,父爱舔着他心灵的创伤,但父爱终究不能代替母爱。每每看到别的孩扎在妈怀里撒娇,看到他们举着妈妈买的玩具时的兴奋劲,看到他们的妈妈在阳光下,为他们一针一针织着毛衣,他总是急急地垂下头去,不忍心再看,拖着孤零的独影,走得远远,就是看到别的孩子被他们的妈妈摁着小屁股,一板一板地抽打,他也侧过头去,不是不忍心⼼,而是自己被妈妈抽打的苦痛都尝受不到。人家能被妈妈抽打,而他不能,他甚至渴望被妈妈狠狠地、狠狠地抽打一顿,可妈妈在哪里呢?
有时,黑黑会收到妈妈寄来的大白兔奶糖和夹心饼干,逢年过节和生日,他还会收到妈妈寄给他一套崭新的童装或者一件新织的毛衣。吃着奶糖饼干,穿着新装,他心里却满是酸楚,更加想念妈妈了。
夏天里,无花果熟了。黑黑小心地摘下,放在米缸里,舍不得吃。他望着满缸的无花果,感到每一颗无花果里,都蓄满了深情的母爱。他无法直接承受到母爱,只能从这一颗颗无花果,间接体验着母爱。他觉得自己所拥有的母爱,一定深藏在远在上海的妈妈心里。
黑黑存有妈妈一张小照片。妈妈曾是个知青,在那个火红火红的岁月里,她跟许多知青一起,高唱战歌,从都市上海来到闽北山里落户。三年过去,知青队的人,能走的都走了,不能走的或留或散,留的人或嫁或娶,茅草棚里只剩下妈妈,生活毫无着落。林场一位好心的大妈带着泪水汪汪的妈妈,来到林场,介绍给了爸爸。后来,妈妈在林场子弟小学当了民办老师。这张小⽚就是从她工作证上撕下的。照片落过水,像面已经淡化,黑黑用一个装味精的小薄膜袋,把照片套在里面,用线把剪平的袋口,一针一针细密地缝好,藏在床底下的木箱里,想念迫切时,他才取出来,捧在手心里,默默地看着,一遍又一遍……妈妈……妈妈呀……
近来,爸爸一直默不作声。这天,吃过晚饭,爸爸把黑黑叫到跟前。爸爸点起一支烟,吸着又吐着,过了一会儿,说:“有个事……”
黑黑盯着爸爸,心里发紧。
爸爸说:“下个月,水莲阿姨就住到我们家来,以后,就跟我们一起生活……”
黑黑愣了一下,头脑里闪出林场食堂那位常给他米糕吃的胖阿姨。
爸爸站起来,粗大的手掌摸了摸黑黑的头,又轻轻地拍了拍,说:“要是不习惯,就到爷爷家住些时候,过了暑假,爸爸跟水莲阿姨去接你回来。”
黑黑默不作声了,一连几天。这天,他从场部兴冲冲回来,拿起搪瓷茶缸,跑到五里外的林场小卖部,打了二两白酒,双手捧着回到家。晚饭时,爸爸伐木回来,黑黑微颤颤地捧着茶缸,给爸爸端上,⼜从⼝袋里,慢慢地掏出⼀个⼩纸包,⼩⼼地放在桌⼦上,摊开纸,是⼗几粒油炸开花⾖。
爸爸盯着他。
黑黑低着头,用脚尖画着地。
爸爸说:“有事?”
黑黑低着头,点⼀点头。
“说吧。”
“黑黑想……到上海去一下。”
爸爸一愣,点起一支烟,好一会儿,他说:“爸爸手头紧,到年底,爸爸发了奖金,去看看。”
“我有。”说着,黑黑俯下身,从床底拖出木箱,又从木箱里抱出两节沈甸甸的竹筒,竖在地上,他抓过柴刀,举起一劈,双手使劲一掰,“哗啷啷”,大小不等的硬币,滚了一地。
爸爸说:“你还小,这么远的路。”
黑黑说:“场部老孙伯伯后天到上海出差,黑黑跟他去,他也肯了。”
黑黑第一次出远门了。
黑黑跟老孙伯伯坐林场拉⽊材的汽车,到了南平,又换乘北去的火车。⾞厢里挤满了人,连过道、洗漱间也全是人。黑黑跟老孙伯伯坐在车厢连接处,他靠在老孙伯伯的怀里,两只胳膊紧抱着竹篮子,时时留神着,怕被人挤压。竹篮子里装满了无花果,这是妈妈留给他的爱,这也是他带给妈妈的爱,他用身体保护着无花果,使它完好无损。老孙伯伯看着他,轻轻地叹了一口气,抚摸着他的头……
火车到上海,黑黑已经疲累不堪。一下火车,他挑着小担子,紧跟着老孙伯伯,挤在潮流似的人群里往外走。他个小,挤在人群中,竹篮子时被人挤着,他时时用手挡着。到了大街上,黑黑睁着眼睛,惊异地张望着。眼前是个新奇陌生的世界,房子又高又大,一座连着一座。汽车、自行车不停地来来往往,到处是人,人山人海,他毫不紧张,因为妈妈就住在这里,他快到妈妈的身边,就要看见妈妈了。
黑黑想着妈妈现在的模样,想不出。他又想,见到妈妈时,妈妈一定会高兴得哭起来,一定会把他拉进怀里,使劲地亲他,当妈妈咬着他带去的无花果时,一定会甜甜地笑,一定会夸他是个疼妈妈的孩子……黑黑走着,想着……
傍晚,黑黑跟着老孙伯伯来到⼀条狭窄的弄堂。老孙伯伯对着手上的纸条,摸到一户人家。
老孙伯伯敲了敲门,对他说:“你妈妈就住在这里面。”
妈妈就在这里面?黑黑心口顿时“扑通扑通”乱跳起来,他从书包里抽出发干的⽑⼱,擦去脸上的汗。
⽼孙伯伯弯腰贴着他说:“孩⼦,⾒到妈妈,千万不要在别⼈⾯前叫妈妈,啊?忍着点,乖孩⼦。”
⿊⿊重重地点⼀点头。⾨开了。⼀位腰繋围⼱、矮⼩利索的⽼妈妈,带着浓重的上海腔,问:“依寻啥⼈?”
⽼孙伯伯指了指纸条,说:“朱琳住这里吗?”
“对喀。”
⽼孙伯伯上前跟⽼妈妈低声说了⼀阵,然后返身对⿊⿊说:“孩⼦,跟这位⼤妈进去吧,伯伯办完事,再来带你回林场。”
⽼孙伯伯⾛了。
⿊⿊跟着⽼妈妈穿过灶披间,来到⼀间带阁楼的⼩房间。⽼妈妈给他盛了⼀碗绿⾖汤,⼜送给他⼀把⼩蒲扇,便去忙了。
黑黑坐在一张⼩靠背椅上,双⼿捧着碗,喝了⼀⼝绿⾖汤,舔了舔干燥的嘴唇。
这时,⼀个三四岁的⽩胖男孩,⼿持塑料冲锋枪,从⾨外闯进来。他刚洗过澡,湿头发梳得⼀丝不乱,全身擦了爽身粉。他⼀⾒⿊⿊,⼤吃⼀惊,⼿上的塑料枪本能地⼀举,对准了⿊⿊,说:“侬侬,是啥⼈?”
⿊⿊笑了笑,说:“我是⿊⿊。”
“⿊⿊?⿊⿊是啥⼈?”⽩胖男孩昂头想了想,想不起来。
“你是谁?”⿊⿊问。
“吾是⽂⽂。”⽂⽂把塑料枪挂在墙上。
猛然间,黑黑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大镜框,里面的照片上,妈妈头上套着一个白花环,手捧一束蔷薇花,偎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身旁,甜甜地笑着……
黑黑盯着照⽚。
文文跑到黑黑跟前,伸臂一指照片:“这是吾阿爸,这是吾姆妈,吾姆妈最爱吾。”
黑黑一惊,睁着眼睛,盯着文文。
文文歪着头问:“侬姆妈爱侬?”
黑黑迟疑一下,拍拍文文的小肩膀,点一点头……他从竹篮子里抓出一个无花果,塞给文文。
文文问:“能吃?”
黑黑点一点头。
文文抿着嘴,咬了一点,尝了尝,便大口地咬起来。
这时,门外响起自行车的支架声。
“文文!文文!”一阵急切而柔情的呼唤声传来。
文文跳了起来,叫道:“姆妈回来啦!”说着,跑出小房间。
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灶披间里闪进⼀位挽髪的少妇,白白的长圆脸上,溢着母爱的柔情,弯弯的月牙眼里,涌着一股渴望的神光。啊,妈妈……
“妈妈!”文文张着双臂扑上去。
妈妈把手提包一丢,笑着弯下腰,舒起双臂,一把揽过文文,紧搂在怀里,弯着脖子,狠命地亲着文文脸蛋上的嫩肉。
“宝贝,洗澡啦,洗澡辰光,有没有跟老妈妈调皮捣蛋?”
“没有,文文今朝没有调皮捣蛋。”
“姆妈闻闻看,涂花露⽔?”
“涂了,文文竖起瓶子,硬劲倒。”
“绿豆汤喝了?”
“喝了两碗。”
“困觉?”
“文文啊,呼滋呼滋困了老长辰光,还做了一个梦。”
“梦见什么?告诉姆妈。”
“梦见阿爸姆妈,带到文文到西郊公园去看象鼻头。”
“还做什么梦?”
“还做了……没了,明朝再做。”
“猜猜看,姆妈给文文买了啥喀东西?”
“是……冰砖。”
“对了,姆妈拿给文文。”
“姆妈最好,文文亲亲侬。”
“哎呀,文文手上是啥喀东⻄?”
“是……果果,老好吃喀。”
“洗了?有没有用开水烫烫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怎么能吃?这是……无花果,是从啥地方来喀?”
“是伊给文文吃喀。”
“啥人?”妈妈紧搂着文文,抬起头,向小房间望来。
“妈妈!”黑黑想叫,但叫不出。他愣愣地站着,生根不动。
妈妈盯着黑黑,柔声地间:“你是……你是谁家的孩子?”
黑黑鼻子酸,抱起竹篮子,向前移了一步。他忍了一下,堆起笑,说:“是……黑黑……”
“黑黑!?”妈妈全身一颤,弃下文文,睁着眼睛,问:“黑黑?你是黑黑?我的……黑黑!”妈妈猛然大叫一声,张开双臂,扑了过来,一把抱过黑黑……
文文吓得蒙起眼睛。
妈妈淌着泪水,不停地搂着黑黑,摸着黑黑,亲着黑黑……
在妈妈的怀抱里,承受着滚烫的母爱,黑黑多想,时间永远停在此刻啊!永远……
黑黑捧过竹篮子,嘴唇颤颤抖抖,说:“妈……妈……这是您栽的……无花果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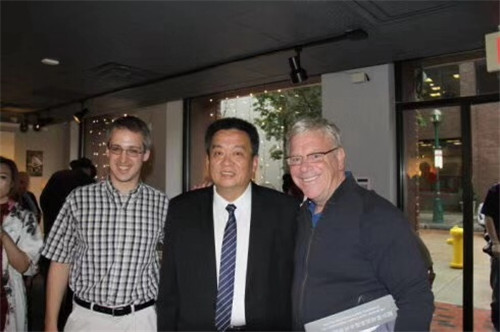

甫卫东关上房门,扣上保险,心口不禁一跳。他瞥了钱小梅一眼。
钱小梅坐在床边上,低着头,翻着一本《毛选》。
一百瓦的大灯悬空而照,房间里通明。墙上的毛主席像被照得光芒四射,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栩栩如生。甫卫东崇敬地望了望毛主席像,心中念道: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!”
窗外的高音喇叭正播着语录歌: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,千条万绪,归根结底,就是一句话,造反有理!造反有理……”令人热血沸腾。
钱小梅放下《毛选》,起身走到窗前,关起窗户,插上铁销,用手摸了摸玻璃窗边沿。玻璃窗糊满旧报纸,密不漏缝。她走向床前,坐下来,脱下军帽,拂了拂羊角辫,又抱起《毛选》,低头翻看着。
甫卫东也脱下军帽,露出平头。他双手捏着帽沿,走到钱小梅身前。
钱小梅缩身一抖,手中的《毛选》滑到地上。她弯腰欲捡。
甫卫东抢先捡起《毛选》,用手抹了抹灰尘,递给钱小梅:“钱小梅战友……小梅战友……你、你《毛选》读过几遍了?”
钱小梅抬头望了甫卫东一眼:“四遍……你呢?”
甫卫东盯着钱小梅的头发:“我已经读了七遍了,现在正在读第八遍……我们‘风雷激’红卫兵团开展读《毛选》竞赛,我读得最多。读毛主席的书,越读心里越亮堂。毛主席的书,就像茫茫夜空中一盏指路明灯,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。”
钱小梅敬佩地说:“卫东战友,我跟你比,还差得很远很远……”
甫卫东说:“毛主席教导我们:‘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’。我虽然读了八遍,但是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同志相比,仍然差距很大……小梅战友,让我们‘一帮一’、‘一对红’,把毛主席的书读到一千遍,一万遍,读……一辈子……。”
钱小梅两腮涨红,点了点头:“好。”
甫卫东跨前一步:“小梅战友……我……”
钱小梅望了望门口:“你舅舅他……他会回来吗?”
甫卫东说:“今天星期六,他回郊区舅妈家,要到星期一早上才回来上班。”
钱小梅往床头挪了挪身:“你坐吧,别站着……”
甫卫东坐到床边上。
外面的高音喇叭播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宣布广播结束。四下顿时安静。
钱小梅说:“好安静啊。我过去总认为,像这样的机床厂,每日每夜,总是轰隆轰隆的机器马达声。没有想到,这么安静……”
甫卫东说:“听我舅舅讲,今天上午,厂里的造反派全部杀到旧市委闹革命,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夺权!”
钱小梅问:“那你舅舅没去啊?”
甫卫东低下头:“我真为他痛心。他是中间派、逍遥派,毫无革命斗志,是工人阶级队伍中极少数落后分子!……我上午气死了,差一点不向他借这个宿舍了。”
钱小梅嘴巴动了动,欲语又止。
突然,灯灭了,房间坠入黑暗。甫卫东摸到墙边,按住拉线,拉了几下开关,灯仍然没亮:“停电了。”他摸到桌前,双手在桌上搜了一阵,搜到一盒火柴。他划着一根火柴,点上煤油灯。房间里散发着雾光。
甫卫东觉得空间缩小许多。他回头望着钱小梅。
钱小梅也望着甫卫东。
甫卫东心口乱跳起来。他走到钱小梅身前,伸出手臂,说:“钱……小梅、战友……让我们团……团结起来……”说着,他抓起钱小梅的手。
钱小梅不由自主地站起来。
甫卫东双手抓住钱小梅的肩膀:“小梅战友……让我们团结起来……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……”
钱小梅一拢头发,抬头望着甫卫东:“卫东战友,我们还没有结……结合呢。”
甫卫东低下头,过一会,他说:“那……我们现在就结合……”
钱小梅想了想,说:“好。”
甫卫东抓起桌上的军挎包。从包里搜出笔和纸,伏案便写——
最高指示
团结起来,去争取更大的胜利
结合宣言书
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——甫卫东、钱小梅……
“等一等。”钱小梅突然说:“卫东战友,我想在这个庄严的时刻,把名字改一改。钱小梅这个名字,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情调。”
甫卫东说:“那改成什么呢?哎,钱红梅!改成钱红梅怎么样?‘红岩上红梅开……’”
钱小梅摇摇头,说:“钱红梅,还是没有改掉资产阶级的情调,红梅前面加上钱,这朵红梅就长在铜臭味里。卫东战友,我干脆钱字不要了,就叫肖梅,小月肖,肖梅!”
甫卫东想了想,说:“肖梅,肖梅,好得很!简短有力,叫起来响亮。肖梅,哎,肖梅还有革命的含义,肖梅肖梅,消灭美帝国主义!”
钱小梅一拍手掌,叫道:“对!对!消灭美帝国主义!从现在起,我就叫肖梅!”
甫卫东说:“肖梅战友,我也想把姓改一下,甫这个姓让人想起是甫志高一个派别的。上次,我们‘风雷激’跟‘井冈山’大辩论时,他们就冲我大喊:‘甫卫东是叛徒甫志高的小舅子’,真令人无比愤慨!为了今后不给‘井冈山’那帮保皇小丑有机可乘,我要把姓改掉!哎,肖梅战友,改成许卫东怎么样?许这个姓,让人们联想起革命先烈许云峰。改成许卫东,给‘井冈山’那帮保皇小丑们一个反戈一击!当头一棒!”
肖梅说:“明天,我们就写个‘严正声明’,宣告我们改名字了,跟资产阶级,跟叛徒分子做彻底的决裂!”说完,她抬头仰望毛主席像:“敬爱的毛主席,我们永远围绕在您的身旁,用热血和生命,捍卫您的革命路线!让红色江山,千秋万代,永不变色!”
许卫东把纸揉成一团,扔到墙角,又铺新纸,飞笔急书——
最高指示
团结起来,去争取更大的胜利
革命结合宣言书
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——许卫东、肖梅。我们出身在红色家庭——工人阶级家庭,我们全身流淌着无产阶级鲜红的热血。我们无限忠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,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!头可断,血可流,赤胆忠心永不丢!
今天,我们在敬爱的毛主席像前正式结合了,这是革命的结合!胜利的结合!我们庄严地宣誓:
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中,我们仍将发扬‘舍得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’的大无畏革命精神,大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,大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!让一个红彤彤的中国永远耸立在世界的中心!
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!万寿无疆!!万寿无疆!!!
许卫东 肖梅
1967年10月25日
许卫东写完,从军挎包里抓出一枚“风雷激”红卫兵团圆章,张嘴对着圆章哈了几口气,用力盖在宣言书的落款处,说:“可以了。肖梅战友,你看看吧。”
肖梅捧起宣言书,看了一遍,问:“这样行吗?”
许卫东庄严地点一点头,说:“行!有‘风雷激’红卫兵团为我们作证。肖梅战友,让我们热烈庆祝一下。”他从军挎包里提出一个行军壶,拔开壶塞,抓起桌上的搪瓷缸,慢慢地倒满水,递给肖梅:“肖梅战友,这是延河水。是我一个战友送给我的,他长征到革命圣地延安,专门跑到宝塔山下的延河里舀的。这比什么水都珍贵。肖梅战友,你先喝。”
肖梅捧着搪瓷缸,深情地注视着缸中的浑水,然后,双唇抿住缸沿,喝了一口水。
许卫东说:“肖梅战友,喝吧,大口大口地喝。让我们的心中激荡着滚滚延河水,就好像我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。抬头望见宝塔山,心中想念毛主席。”
肖梅闭上眼睛,慢慢地喝了半缸水,将搪瓷缸递给许卫东:“真好喝。卫东战友,我仿佛望到那尖尖的宝塔山,还有那灯火辉煌的延安窑洞,毛主席就坐在窑洞里,挥动巨笔写着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……”
许卫束捧过搪瓷缸,望了望毛主席像,然后昂头一饮而尽。他放下搪瓷红,盯着肖梅,说:“肖梅战友,我们,已经正式结合了!”
肖梅迎着许卫东的目光,点一点头,说:“我们结合了。”
许卫东突然慌乱起来:“肖梅战友……”
肖梅说:“卫东战友……”
“我们……团结起来……”
“团结起来……”
“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……”
“一个人那样……”
许卫东叫道:“肖梅战友!”他伸出双臂,猛然抱住肖梅。
肖梅打了一个冷颤,僵硬地挺着身子。
许卫东越抱越紧。
肖梅仍然挺着身子。
许卫东说:“肖梅战友,毛主席教导我们: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作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……文质彬彬……”
肖梅叫了一声,猛然抱住许卫东的腰。
许卫东说:“我们团结起来了……像一个人那样……”
肖梅闭着眼睛,头顶着许卫东的胸:“卫东……战友……”
许卫东的手伸向肖梅的腰间。
肖梅一把抓住许卫东的手。
许卫东急促地说:“肖梅战友,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’……‘不能那样雅致’……‘那样从容不迫’……”
肖梅说:“卫东战友,我自己来……”她松开手,解下腰间的武装带,又解衣扣,解了两个,她停住手,走到煤油灯前,“呼”地吹灭了灯。黑暗中,她摸到床前,脱下衣裤,躺到床里边,拉过被子盖在身上。
许卫东脱光衣裤,跳上床,掀起被子,凶猛地抱住肖梅:“肖梅战友!”
“卫东战友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!”
“卫东战友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!肖梅战友!”
“卫东……啊哟!”
“肖梅战友,怎么啦?”
“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,坚强些!”
“啊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,坚强些!再坚强些!‘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……’”
“‘下……下定……决心……不怕牺牲……排……排除万难……去争取……争取胜利!’啊……啊!”
“肖梅战友!肖海战友!肖梅战友……噢!肖梅战友!肖梅战友!肖梅战友!肖梅!你好!肖梅……战友……”
“卫东战友,让我们永远永远团结在一起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,永远……永远……我们永远永远团结……在一起……”
“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,卫东战友……卫东战友……卫东战友……让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……卫东战友……”
突然,灯亮了,房间里通明。许卫东一个翻身坐起来,望了望门口,说:“来电了。”
肖梅双臂相抱,盯着许卫东。
许卫东低头看着肖梅:“我……我去把灯关上。”
肖梅没有吭声,紧盯着许卫东。
许卫东也盯着肖梅。
突然,肖梅伸起双臂,紧紧抱住许卫东:“卫东战友!”
许卫东拉过被子,转身抱住肖梅:“我……我们……我们再团结起来……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……”
肖梅叫道:“我们、我们再团结……再团结起来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!肖梅战友!肖梅战友……”
“卫东……卫东战友……”
一阵后,两人喘息着,相偎在一起。
肖梅说:“卫东战友……长征的时候,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战友……还记得吧,去瑞金的路上,我……我小便急死了,可是裤带打了个死结,怎么解也解不开……我急死了……”
许卫东笑了笑,说:“急得都哭了。”
“没哭。”
“哭了。”
“没哭。”
“哭了,哭了,眼泪都掉出来了。”
“没哭,毛主席的红卫兵无比坚强,从来都不哭。”
“好,没哭。”
“卫东战友……你当时怎么想起……帮我解裤带?还用牙齿咬死结……还当着那么多战友的面……”
“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应该互相关心,互相帮助,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做的。”
“卫东战友,你真好……”
“肖梅战友你也好……”
突然,肖梅将头埋进许卫东怀里,哭了起来。
许卫东抱住肖梅的头:“肖梅战友,怎么啦?怎么啦?”
肖梅说:“卫东……战友……有一件事情,我要告诉你……”
许卫东急问:“什么事?”
肖梅泪如泉涌:“卫东战友……我爷爷……我爷爷……是小业主……”
许卫东猛然松开手,惊疑地看着肖梅:“小业主?怎么会是小业主呢?你……你不是红五类吗?你爸爸不是还当过童工?苦大仇深,怎……怎么你爷爷又变成了小业主?”
肖梅说:“可我爷爷也很苦……”
许卫东说:“小业主怎么会很苦?”
肖梅说:“可我爷爷就很苦。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。”
许卫东沉思着。
肖梅摇了摇许卫东,说:“卫东战友,请你相信我爸爸的话。他还说,那时候,他们全家经常吃不饱,经常向地主借粮食。有一次,我爷爷去向地主借粮食,地主不肯借,还骂我爷爷。我爷爷无比气愤,冲过去,打了地主一记响亮的耳光……”
许卫东急问:“什么什么?你爷爷打过地主的耳光?”
肖梅点一点头:“千真万确,这是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。后来,我爷爷被地主家的狗腿子关进去,打了半死。”
许卫东嘘了一口气:“这就行了,‘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迫,激起农民的反抗’,这是革命行动,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。这说明你爷爷对地主有深仇大恨,是红色小业主,跟中农差不多。”
肖梅猛然抱住许卫东:“卫东战友,你真好,真好……”
许卫东轻轻拍着肖梅的背:“肖梅战友,你也好……”
突然,外面的高音喇叭响起来。一个男声高喊:“革命的造反派战友们!我厂‘红色风暴’造反兵团今天杀向旧市委,批斗了我市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张国田!现在他们凯旋归来!让我们向他们致敬!‘红色风暴’万岁!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!万岁!!万万岁!!!……”
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。
“嘭!嘭!嘭!”有人敲门:“王师傅!王师傅!开开门!”
许卫东和肖梅紧紧相抱,惊恐地望着门。
门外有人说话:“王师傅!开开门!开门呀!……哎,怎么没声音?你看,门上没锁,灯又开着,肯定在。王师傅!开开门!借个煤油炉下面条……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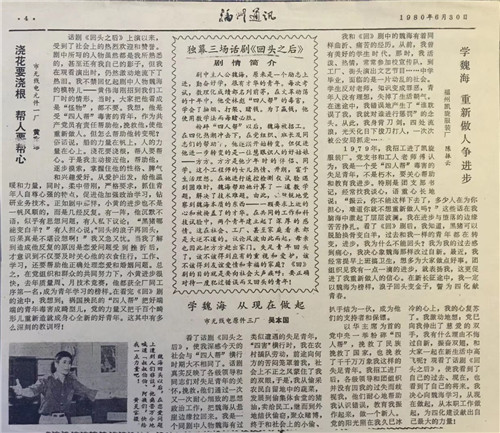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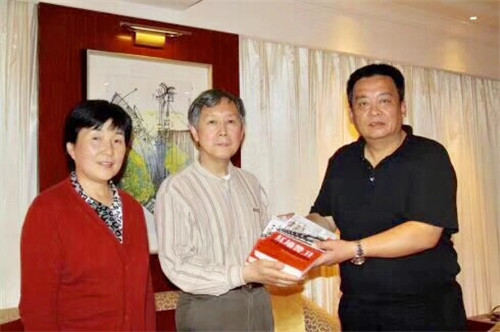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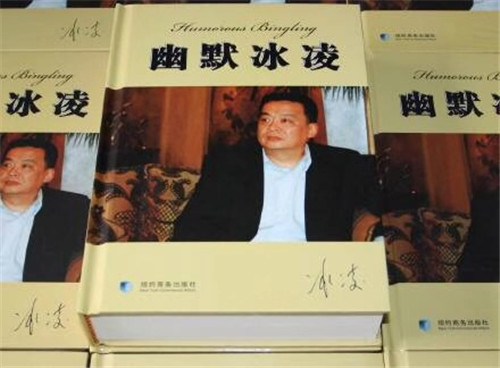

上一篇:腾飞圆珠笔手绘苏州四大古典园林









